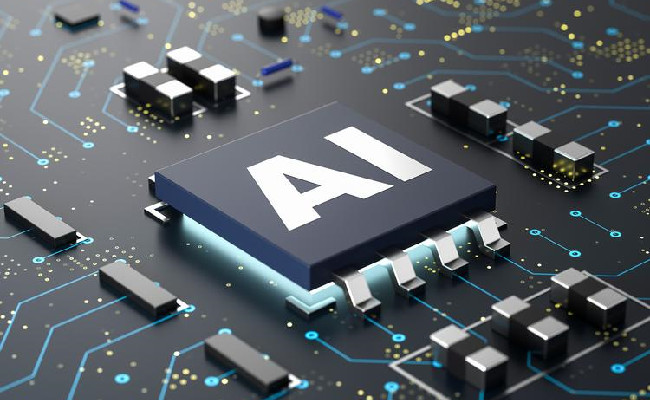给AI写台词是怎样一种体验?Siri创意总监现身说法
唐旭 李林 编译整理 量子位 出品 | 公众号 QbitAI
一句过年好,能换来Siri花样百出的回应。
这些有点冷、有点萌,又似乎在抖机灵的回复,都是哪来的?
AI自动生成?目前技术还没那么先进。
在这些智能助手背后,藏着一个神秘群体:AI的编剧。他们负责给智能助理写台词,安排着当人们想问天气、定闹钟、放音乐等等时候,AI该如何回答,还得让智能助理能偶尔说出令人眼前一亮的金句。
《华盛顿日报》之前有一篇报道说,给AI写台词已经成了硅谷的一项热门工种,在Siri、Alexa、Cortana等智能助理背后,除了程序员,还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剧人、小说作家等文艺工作者参与其中,为这些AI赋予人格。
给AI写台词,是怎样一种体验?
和文学创作一样,AI的写手们得为智能助理幻想出一个人生故事。比如说医疗类聊天机器人、对话式生产力工具的写手,就需要思考他们的智能助理是工作狂、讨好上司的员工还是谦虚低调的实干者。
就算是平淡的日常任务,也需要深思熟虑,写手们在智能助理最死板的行为中,也悄悄为它们构建着人格、癖好。
比如说提供日程规划聊天机器人的创业公司x.ai,也需要思考称呼人类时该用姓还是用名、回复时要不要用表情符号。这家公司的交互设计师Anna Kelsey说,我们不希望人们说,你家智能助理太随意或者太端着了。
微软的智能助理Cortana背后,就有一支6人的写作团队,包括一名诗人、一名小说家、一名剧作家、一名电视剧作家。他们每天早上在Redmond开会,为Cortana该如何回应一些新问题来一场头脑风暴。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日语等其它语言版本也有人负责塑造Cortana的个性,他们也会远程参与到这场头脑风暴中来。
总有金句的Siri背后,当然也少不了类似的团队。
Siri的写手、创意总监Mariana Lin最近在著名的文学期刊《巴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向我们展示了智能助手背后这些剧作家的日常,以及她如何看待人机对话,对AI和人类的交互有着怎样的期望。
她说:为AI写对白时,就有点像在写一出荒诞派的戏剧。
量子位带着大家来读一下这篇《与Siri的荒诞派对话》:
Nagg:我的糖梅! Clov:厨房里有只老鼠! Hamm:一只老鼠!现在还有老鼠? Clov:厨房里有一只。 Hamm:然后你还没消灭他? Clov:干了一半。你打断我们了。 Hamm:他不能离开? Clov:不能。 Hamm:你等会儿解决他。让我们向上帝祈祷。 Clov:又一次! Nagg:我的糖梅!
——萨缪尔·贝克特,《终局》
注:萨缪尔·贝克特是荒诞派戏剧重要代表人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这些年来,给Siri和Sophia这样的AI角色写对白已经成为了我的日常。这并不是件寻常的工作。
首先,你要了解这些生存于人类之中的非人类生命的性格;更乱的是,你必须追寻人与机器人之间那种理想的对话情境——在语音交互设计中,这叫作愉快路径(Happy Path)。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还存在不愉快路径。
在文学作品中,对话的作用是丰满人物、推动情节,根据创作者的需要,可能在一些作品中还有别的作用。但对于AI而言,对话通常被视为达成某种目标的一种途径,或是实现某种功能,或是帮用户拉近人机关系。
关键是,我们要尝试去构思出对于人机对话而言的最佳路径,而当面对不同的文化、语言、性别和身份,这些对话听上去将会截然不同。
因此,为AI写对白,就有点像在写一出荒诞派的戏剧:你有现成的角色,心中也有些目标,但你完全不知道其他角色——也就是人类将会说什么、做什么,也没地方去查。如果把对话拉回正轨是我们这类人的责任的话,正轨在哪?换句话说,愉快路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答案就是,没人真的知道。
如果,对于给一个虚构的角色编写对话而言,最高的目标是抓住关于角色的真相,那你要做的就不只是抓住这个机器人的真相,还要抓住每一段人类对话的真相。
当下,这基本是不现实的,于是所有不愉快路径就全来了——但我支持它们。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是言语之中,荒诞都充满了各个角落。尤其是当背景不同观点各异的人聚集在一起时,这种现象还会被放大。因此,我们或许应该重新考虑大部分对话式机器智能背后的硬逻辑,荒诞派对话之中其实蕴含着典型的人类特征。
当然,AI听懂你说的话并完成任务的感觉很爽(辛苦了Siri/Alexa,谢谢你们每天对我说早安、帮我开灯、替我安排日程)。但这种满足是一种……怎么说呢,在短暂的快感之后,你将不得不面对每天早上都要以重复的命令去要咖啡的痛苦。
这些功能性的对话,并不会像日常交谈一样给我们太多的启迪。相反,正是那些荒诞的、令人意外的语言照亮了诗歌、文学,满足了我们不自知的内心需求,带来了超凡脱俗的艺术享受。
乔布斯深明此理,他生前一直在提倡均衡地打通技术和自由艺术之间的界限。他不喜欢研究用户,在他看来,人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他的工作就是把那些人们从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交给他们。一些人批评他自负、傲慢,但乔布斯是个真正的创造者。
想像一下,艾米莉·狄金森会根据关于读者喜好的调查报告来决定自己下一首诗的主题和韵律吗?艺术从不来源于共识。
非线性的、独白式的漫谈是人类对话的另一大特色。我们举一个剧作家阿德里安·肯尼迪的例子:
Jean Peters:我呼唤主,夜枭回应了,它在我的高塔周围萦绕,呼啸,它的羽毛拍打着外墙,它有羽毛、大而空洞的双眼……黄皮肤和黄眼睛,会飞的杂种。在塔中,我不断地呼唤,唯一的回应就是那只夜枭。 七月八日,我收到了母亲的电报。电报上说,你的弟弟出了事故,在圣·卢克的医院从昨晚开始就失去了意识。爱你的,母亲。我回到了家。我的弟弟在穿着白色的长袍躺在白色的单子上。
—阿德里安·肯尼迪, A Movie Star Has to Star in Black and White
认真地说,对于贝克特和肯尼迪戏剧中的对白,我最喜欢的是他们无序地再现了人类生命的混乱和不可理解,这比有着明确目的的对话美多了。他们的角色相互排斥、矛盾,每个人说话时都只存在于自身的宇宙中。对话就起源于这些仿语症似的意外中,而并非真正的互相倾听。
一些人可能会说,他们没兴趣和自己的AI进行这类对话。有理有据。但我是不想天天从AI那订大瓶装洗洁精。
现实是,如今多数的人类交流都是通过技术实现的,与之伴随的,是光纤的削减和二进制的压缩。一段五维、节奏起伏飘渺的对话被压缩成功能性、驱动性、缺乏耐性的东西。美国诗人理查德·雨果曾说过:一旦语言只为传输信息而存在,它就离死亡不远了。
我不知道迂回、文雅、零散的人类间的对话是否会随着事务性人机对话的进步而没落。如果我们继续同这些技术型的人格交互,这些类型的对话会改变我们脑中对于对话的看法,乃至重塑我们同其他人交谈的方式吗?我们会将自己的词汇库调整成其他人能理解的模式,只发出明确的请求而不是问出开放式的问题吗?想像一下,你转头对自己的朋友说:去Mankas家的路;或是,诗歌,李立扬。
我恐惧的不是世界被机器人支配的奇点,而是对话被机器人支配的奇点。我不希望AI把人类的语言变成纯粹的功能,不想让对话被特定的目的拖着走。
AI不该继续伤害已经在消亡的语言艺术。AI应该向着人类文学、艺术中最好的部分,为我们的生活创造富于灵感的对话。相比于愉快路径,我们更应该追求趣味路径——足够幸运的话,每个人都可能发现它。比如,下面就是一段你今天可以和Siri试试的对话:
人:我回来了。 Siri:尽管再简陋……(没有地方比得上家) 人:这里有爱吗? Siri:有趣的问题。 Human:我不知道我在找什么。 Siri:这不是问题。 人:你确定吗? Siri:我时不时吧,就很喜欢这种模棱两可的话。 人:暴风雨要来了。 Siri:不,我觉得现在没有暴风雨。 人:但它在你的内心里。 Siri:谁,我? 人:人们都问你什么? Siri:我们的宇宙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奇怪问题,而我,所有问题都被问过。 人:学狗叫。 Siri:下回你就要让我学猩猩吼。 人:喵~ Siri:好猫咪。
本文来自量子位,创业家系授权发布,略经编辑修改,版权归作者所有,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 下载创业家APP,读懂中国最赚钱的7000种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