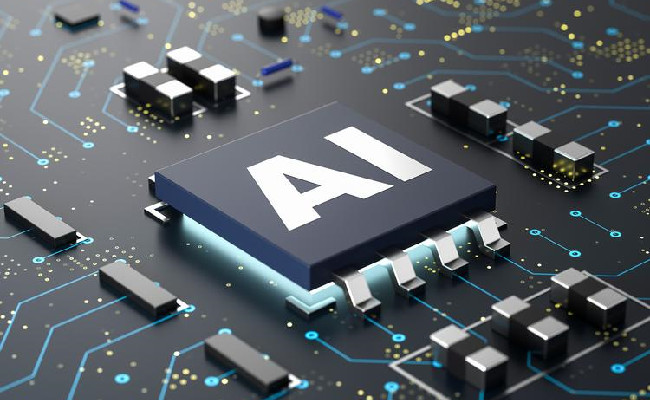一个哲学教授决定去拍短视频

过去多年,这个哲学老师都是在大学课堂上传授知识。当那些被他影响的学生毕业后消失在社会上时,他偶尔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离大众太远了?
2022年初夏,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站到了短视频的流量上。这像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这个世界是如此真实,现实是如此具体。人们告诉他,经常看他的视频,好像自己变得不再偏激了,好像能从繁复的生活中获得一些思辨的快乐。
新的表达渠道,新的受众,虽然也有新的伤害,但他依然选择往前走。他确信自己正在影响一些真实的生命。


这么多人愿意听哲学
这个男人的相貌并不算出奇,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身着一件深灰色的polo衫,有时是红色格子衬衫,戴一副框架眼镜,背后是一双锐利的小眼睛,头发已经有些稀疏。
他通常站在讲台上,面前摆着一台电脑,一盏茶杯,也许是一堂课。又或者是在饭桌上,在车上,就像一场生活里的闲聊。独树一帜的是他所说的话。没有特效,美颜,剧本,演员,反转和情绪。也没有遥远的风景,可爱的猫,没有你经常能在手机里看到的那些刺激视觉与神经的东西。他只是普普通通地坐在屏幕前,说一些话。他平时也这么说话。
他是这样说的:
人是目的,还是工具?
柏拉图曾经用逻辑证明,灵魂是存在的,用双手就可证明。(然后他伸出双手,重现了柏拉图的这场证明。)
哲学是时代的挽歌吗?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
这是一些看上去距离现实很遥远的话,却让他很快在抖音视频上有了二十万粉丝。他叫苏德超,是武汉大学哲学院的一名教授。他以前从未想过,有这么多人愿意在抖音上听他的哲学课。
2022年5月,苏德超受到一家商业机构的邀请,去广州讲课。一个天气晴朗的周末,他坐上从武汉前往广州的火车。听众的身份显然与他在武大的学生有很大不同。
台下坐着云南茶厂的老板,民营医院的老板,还有卖眼镜的,做健身的,做教培的,做女性心理咨询的,归国的留学生,海外银行的区域代表,年龄从二十来岁至六十岁不等。
他决定讲:什么是西方?
在一些人看来,这也许是个不讨好的话题。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还有多少人愿意去了解西方?可他认为这很重要。随后,他的话题延伸到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古罗马的法律,宗教与教皇革命,以及近代衍生的自由与民主。
起初听众是充满怀疑的。那些人看着他,不说话,不点头,眼神里充满质疑。他后来打了个比方说,大学里的学生像是禾苗,但面对社会上的人,就像是面临着一道深渊。他不知道他们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也许是他讲得过于专业,或者哲学距离大众就是太过遥远?
但两天的课程下来,结束的时候,听众们却将他完全围住。他甚至有些被这样的热情吓到了。
他们问他提到的古希腊学校,问为什么要鼓励学校去研究无用的东西?他还在人们的讨论中察觉到了更多的东西,来自于提问背后,人们身上的不安感。那是春天,远方有战争,上海的街头空无一人。人们想知道,这一切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世界还能保有稳定性与持续性吗?生命的交代是什么,赚了一些钱,然后呢?
他并没有给听众们具体的答案。哲学从来不是对具体的问题进行指导的。但他隐约感觉到,在剧烈变化的生活里,对哲学的需要从深处被激活了。

酒店的会议室里还有几个年轻人,他们5月17日刚刚成立了一家新的MCN公司。他们将苏德超这两天的课程录了下来,同时希望能用这些视频为苏德超开一个短视频账号。
其中一个女孩叫卉雅慧。她29岁,听完了全程,差点快睡着了,但醒着的时候,她还是觉得苏德超的课堂很有意思,具体哪里有意思,她也说不上来。她之前做的是教务,这是她第一次尝试做短视频。她说服苏德超,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哲学呢,就当是一次机会,一次尝试。有些稀里糊涂的,苏德超同意了。
但是,用哲学起量真的很难。卉雅慧说,她用了一些互联网的词汇。
他们尝试做了六七个账号,按照每个年轻人的判断挑选苏德超课程里的片段。从0到10000个粉丝是最难的。第一条受到关注的视频是一个摄像男孩剪出来的。他对哲学和历史很感兴趣,录完苏德超的课程,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三角形的例子。他单独剪出了这一条。

在这条视频里,苏德超说,你从来没有测量出一个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你凭什么说它就一定是180度呢?人的定义一定是客观事实吗?
这条视频迅速被很多人看到了。不过,最早的回馈都是些质疑的声音。有人说,哲学有什么用?(他们最常收到的回复就是这条。)还有很多人说,哲学老师也没有学过小学数学吗?
反差,与一般观念并不相符的这些东西,吸引了更多人来围观。团队被激励了一把。他们尝试了更多条视频。苏德超又去了一次广州,这次从接到苏德超,到上课,吃饭,路上开车,团队全程录像。
饭桌上,苏德超和人聊到数学——数学是最难科普的学科吗?他吃了几口,放下筷子,拍手,大笑。他再次谈到三角形内角和来自定义的问题,讲到数学是一套概念系统,而不来自于任何现实经验。
这次交谈被剪成一条短视频。这条视频发出去后,点赞很快超过了三十万,播放超过了一百万。一次哲学谈话,这么多人观看。这是个非常令人惊异的数字。

成为桥梁
过去多年,苏德超在武汉大学上一堂讲述形而上学的课。这是一门通识课程,教室宽敞,学生来自这个大学的各个学院,文科、理科、工科或者医学。教室位于一栋相当老旧的教学楼,楼外有很多桂花树。在桂花的香气中,苏德超开始讲形而上学的系统与历史。
很多学生都还记得他讲到经典的哲学之问,讲到那艘忒修斯之船——一艘船的零部件被更换后还是否是原来的船?这些课堂是一场又一场理性、逻辑与理念的游戏。有一天教学楼突然停电了,其他教室发出散场的欢呼声,但苏德超的教室没有人离开。在黑暗中,他就那样继续讲课。学生们举起手机给他打灯,就像是一个舞台,而老师就在舞台的各个角落里穿梭。
但苏德超逐渐意识到,这样局限在大学的课堂,局限在线下的交流,在这个时代已经远远不够了。

改变的第一步是从自己开始。他开始参与到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随后是给大众讲课,他还在网上写文章,试图向公众说理,他知道,如果你想影响更多人,你得从大学这个相对封闭的象牙塔里走出来。
他开始对一些公众事件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对他来说当然不难,哲学最擅长的就是从无数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他下载了一款软件,只要对着手机说话就能随时转成文字。就这样,他利用一切的空余时间对着手机说话:在课堂的五分钟间隙里,在食堂吃饭,在车上等人,或者只是在校园里走路时。学生们已经习惯了他的自言自语,叫他豌豆射手。他曾经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学院的活动室里打乒乓球。但现在他连打乒乓球的时间都没有了。
但在如今的公共场域发出声音,可能带来一些困扰。比如他曾经对28年错换人生的新闻发表看法,谈到养育与生育同等重要。追查真相是必要的,可在追查真相的过程中是否会伤害到原有的亲情?
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观点。但他忽视了这件事已经成为一场当事人双方和各自追随者的战争。几千条评论涌进来,还有无法计数的私信。人们说他愚蠢,是非不分,逻辑混乱。更多的是辱骂和诅咒。他起初还会一个个回复,但这就像是他无法阻挡的一场潮水。紧接着有匿名举报电话打到了武汉大学的各个部门,一些身在武汉的人来到学校递检举信。
有人说,苏老师,要不就把之前的发言删了?他说不能删,我又没错。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周。他有些难以承受了,说再也不对此事件发表看法。但言语的暴力还在持续。
半年过去,有天夜里他醒来,就像不知道夜晚有多深,心脏呼呼乱跳。他忽然发现枕头是湿的。他流泪了。我为什么流泪了?他问自己,不可能,又没发生什么事情。就像一种没有缘由的悲伤。他后来觉得,也许是那些匿名的伤害还停留在潜意识里。
所以,当广州的几个年轻人提出要给他开抖音账号时,他起初有些犹豫。不过,他毕竟经历过这一切。他从没想过要退网,清空账号,或者停止说话。时间越久,他越来越将这件事看作一场实验。
他后来说,鲁迅对他的启发很大。他开始更多地考虑另一个问题:如果精英与大众之间越来越遥远,是否最终会产生剧烈而不可缓解的冲突?在全世界,这似乎都是真正发生的问题。两极化的政治,剧烈的情绪,精英操控民粹,特朗普的上台。
他说,如果老师的位置注定是成为桥梁,那么在互联网上说话,是否是另一种桥梁?以及,这个时代究竟需要怎样的桥梁?
而在桥梁对面,都是什么人呢?那些人能否代表中国最真实的状况。他后来逐渐认识到,抖音的背后也许就是中国的真实。这些真实的人究竟在想些什么,他又能否去影响和改变大众思考问题的方式。

影响真实的生命
2022年夏天,从广州回到武汉后,苏德超开始自己录视频。
他的办公室位于武汉大学的振华楼,那是一栋刚刚修建成的大楼,离正门不远,落地窗外是高大的樟树,武大图书馆标志性的绿瓦砖顶,还有不远处的珞珈山。
办公室里堆满了书。书桌,茶几,书柜里都是凌乱的书。四个大型松木书柜,最左侧是那些与哲学专业相关的,《语言的逻辑分析》、《意义、实在和知识》、《死亡研究手册》,黑格尔、康德、语言哲学。但往右侧走,书籍的主题明显宽泛许多,量子力学、数学、大量与教育改革相关的书,一整套《牛津西方历史》,还有佛经,经济学和企业管理。

有时学生会帮他录视频,但多数时候,是他自己处理与视频录制有关的一切。
他显得有些笨拙,拿出一个录音耳机,试音,别在领口上,再拿来一把仿皮质的椅子,坐在书柜前,用书柜格子与头顶的距离来判断位置歪了没有。三脚架放在房间的另一侧,将手机开启摄影模式。说完一段话,回到三脚架的位置,暂停,重来。
他把抖音上那些粉丝们的提问打印下来,放在腿上,一个一个回答:
苏老师,如何发自内心地去否定掉一个自己一直都肯定的想法?
真理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真理?真理是逻辑吗?是工具吗?
苏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阴影属于什么呢?是物质么?
也有人会问到一些更现实的问题。比如因为疫情长期居家的孩子,少了社交室外活动,该如何使他们免受次生灾害?还有年轻人关心的恋爱问题:被异性拒绝了,就无法相处下去了吗?
他乐于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如此真实,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面对的不是形而上学,而是非常具体的生命和体验。
苏德超的个人生活同样也是真实的一部分。他48岁了。就在2019年武汉封城的前一天,他回到四川,面对母亲的离世。而在2022年的末尾,武汉刚刚放开,12月14号,他的父亲也离世了。他说:父母就好像是钉子,将人钉在世界上。当父母都离世后,我与世界的关系变弱了很多。
他的心脏也出了一些毛病,好像每跳动十次就有一次不正常。医生建议他住院,做手术。他没听。他吃了很多药,可等到他觉得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心脏又莫名其妙好了,医生也解释不了,并且不建议停药。他还是把药停了。那些药还堆在他的办公桌下,一大包塑料袋。他开始阅读神秘主义,更想用哲学来寻找人在世界上的位置。他要用清晰的语言表达某些体验。
真实的生活正在缓慢回来。核酸亭退出了校园,但大学里的人很少,学生们几乎都已经回家。2022年的最后几天,苏德超在校园散步。空气湿冷,没有星星与月亮,道路上空空荡荡的,樱花树落光了叶子,裸露的树枝像在夜空中跳舞。
一个女孩突然走了过来。她身穿白色羽绒服,原本正在看手机,听到苏德超的声音,她忽然看了他很久,跟着他,又小心地靠近。
您是不是哲学院的苏老师?她说。
她自我介绍是历史学院的博士,最近总是看他的视频,比如最近的一条,苏德超提到如何去阅读一本书。她说她受益很大,她很兴奋,和苏德超打完招呼后就礼貌地离开了。

这就是短视频的影响。他说,但做视频比写文字更难,我在这边用功一点,接收的那端就会轻松一点。
但这会不会像石头投入水中?即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可你也很难判断那些视频究竟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他说,有些人会告诉他,经常看他的观点,好像自身变得不再偏激了,好像能从繁复的生活中获得一些思辨的快乐。他确信自己在影响一些真实的生命。
要让人看到不一样的世界,真正的世界,真正的路,如果我们心中没有想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会视而不见。如果人们能对观念做好准备,如果世界出现了一些风险,也许他们能够避免,也许他们就能够在那时做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他最后说,我依然相信这些。
他继续往前走,走过潮湿的夜晚。无论如何,苏德超已有了新的表达渠道,以前是课堂,现在还有抖音,他开始面对更多的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受到过伤害,他也依然选择往前走。